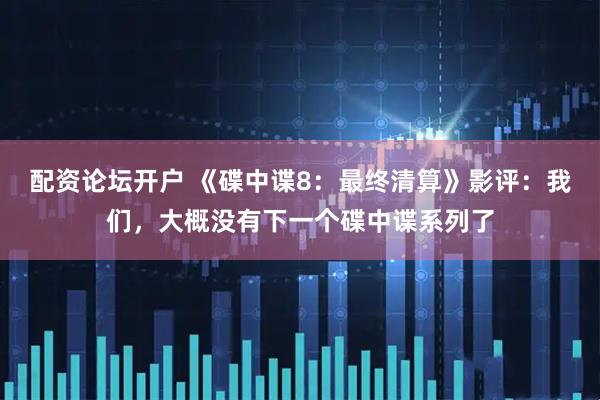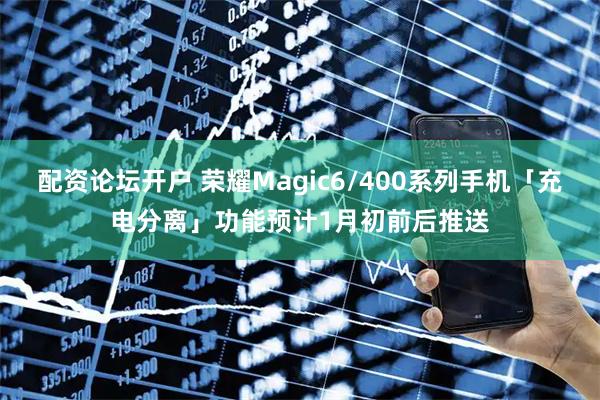1949年10月2日的夜色,初秋的北京城仍弥漫着礼炮的硝烟。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财政经济小组的第一次碰头会正在进行。堆满厚厚一摞密封袋的木制长桌旁配资论坛开户,几个新政府的要员翻检着民国财政部仓促留下的卷宗。档案袋封面那行醒目的数字——“7.3亿两白银未偿对外债”——在昏黄灯光下显得冰冷刺目,仿佛是旧中国沉重的锁链。与会者大多沉默,直到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这摊子,谁来埋?”
毛泽东没有急着表态。他抽空翻开记录本,一页页看过去,眉头却并未皱起。新中国刚站稳脚跟,粮食配给紧张,铁路桥梁残破,工厂机器长期停摆,而列强驻华银行却寄来成捆账单。账单里最醒目的几笔,追溯到七十多年前:1895年的《马关条约》、1901年的《辛丑条约》、1911年前后各省清政府抵押的关税、盐税、厘金。堆叠起来,共计七亿三千万两白银,换算成当时国际金价,大约合五十亿美元,比新中国成立时的全部可动外汇还多出数倍。
问题并非单纯数字。清末民初的“借款”几乎都附带海关、盐务、铁路、关卡、内河航运等抵押条款,还规定倘若违约,就可派驻“洋监督”,调动兵舰“维护债权人的安全”。这些条款在近代史上留下的,是一个个含着血和泪的地名:威海卫、旅顺、大沽口……如果照单全收,不仅要把国家预算掏个底朝天,还得把已经收回的一部分主权拱手再让。这正触及新政府赖以立国的根本——独立自主。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讨债信在民国时期就没断过。1928年,宋子文接到英美公债团催款时曾摊手长叹:“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然而话音虽硬,海关征税却年年拿去填补旧债窟窿。至1936年,关税收入的七成被债务黑洞吞掉。再往后,连对日战争中,南京政府仍按期把银元汇向东京,这一讽刺足以刺痛每一位中国人的神经。
1943年底,开罗会议上,美英为了稳住蒋介石对日作战的决心,愿意“象征性”豁免一部分赔款,并宣布中止庚子赔款。罗斯福的电文声称“出于正义”,但美国国务院备忘录的备注极为赤裸:“争取中国舆论向美倾斜。”当年的帝国算计新中国看得一清二楚。1949年11月初,法国外长毕铎向周恩来提出复谈旧债,语气颇为客气,却着重强调“国际契约神圣不可侵犯”。周恩来翻开对方带来的条约副本,指着落款年份说:“这是1913年的公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国民政府,我们只对人民负责。”
毛泽东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闭门会议上给出了结论:“这堆烂账,一笔不认。”他提出四个字——“历史作废”。法理基础来自《共同纲领》第五十五条,对旧中国签订的条约与贷款“分别审查,作出废止或重新谈判决定”。换句话说,什么该谈、什么必须废,主动权在北京,而不在伦敦、巴黎或东京。接下来半年里,外交部与财委会开了十几轮会,以十余份备忘录列清了三类账:一是列强胁迫清廷签订的不平等赔款,统统作废;二是民国政府在内战时期用“外国银行”渠道所借、并被用来镇压解放区的军费,拒绝承认;三是抗战期间为联合抗敌而由同盟国拨付、尚未结清的军事援助,保留谈判空间。分类之后,再对照国际法逐条公布,昭示天下。

就在北京向外递出第一份通牒时,伦敦出现戏剧性一幕。1950年1月4日的《泰晤士报》头版报道:“新生中国疑似拒付清季旧债,或涉7.3亿两银。”英债权人协会立即开会,主席老布莱尔拍桌子:“要他们偿!”然而英国外交部的评估报告却泼了冷水:“切勿轻举妄动。中国政局既定,强行逼债只会推中国更靠近莫斯科。”面对现实,英方虽然嘴上强硬,实则迅速把谈判级别降格。一个世纪的炮舰政策,不再凑效。
苏联是另一重考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外界多关注军事条款,忽视了起草过程里双方围绕沙俄时期对华债务的暗战。谈判第七天,苏联顾问提出保留1896年《中俄密约》所涉东北铁路资产权益。毛泽东端起酒杯,只说了一句:“帝俄的遗产不属于今天的苏维埃,也当然不会再成为中国人民的负担。”一句话点到即止,斯大林沉默片刻,挥手示意放弃索赔。档案里记录这一幕时,只用了一行干巴巴的文字:“Сам вопрос снят.”(此议题撤销).

进入1951年,外交战线的进展与国内土改、抗美援朝同时推进。财政情况虽紧绷,但新政府坚持一条铁律:合法现贷,该清还;非法旧债,分文不付。于是同苏联谈妥的原子能贷款,用的是钨砂、锑矿、滑石等战略物资分期折抵;东欧各国的设备供货,则用棉纱、茶叶、外贸成品偿付。外人看着繁琐,中国方面却咬死兑现,账本分毫不差。1957年4月,波兰外长拉帕茨基访华,尚未落座,便对周恩来竖起大拇指:“你们是华沙看到过的最守信用的伙伴。”新中国的“信誉资产”自此写进欧洲谈判桌。
对日本,态度更鲜明。1951年旧金山对日合约草案中,部分盟国提议让新中国继承清朝欠日债务,并用其冲抵中国未来可能索取的战争赔偿,这份文件送到北京后,朱德在批示里写下四个字:“岂有此理”。1952年,《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署,明确债务、赔款各自归零。把“旧账两清”作为谈生意的门槛,日本商界本以为能讨到便宜,却反被要求以等额出口设备换取中国原料。时任全权代表高碩仁回忆,“日方谈判代表频频擦汗,连说‘理解、理解’”。
那些年还有不少侧面细节。天津英租界的电灯公司原本声称拥有半世纪特许权,接到“债务与特权一并废止”的通知后悄悄撤走最后一批工程师;苏州河畔的老汇丰仓库,昔日悬挂英旗,如今改作纺织机械库房;上海外滩的门牌焕上新的国徽,昔日推销公债的洋行职员排队办离境手续。种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法律、外交与治理在背后同步推进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百姓并未因拒付旧债而背上额外重税。1953年国家第一部预算案公布,中央财政收入近222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税与工商税占绝对大头,没有一分钱被列为“赔款”支出。街头茶馆议论纷纷:“清朝欠的,民国又添一茬,如今总算斩掉了。”有人感慨,真正的腰杆子,就是别再为他国的枪炮买单。

1956年,中国恢复对外贸易常态,通商口岸的洋行已不足战前三分之一。不少欧美资本家看清形势后转向合资、补偿贸易,试图重新进入市场。可面对清晰的法律底线,他们只能按新规则谈判。这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依旧有限,却在国际收支上保持了大体平衡。历史学者统计,从1950到1959年,中国对外“拒付”金额相当于旧债总量九成以上;同一时期,通过正常贸易和合约偿还的新债款项,则一笔不差打入对方指定账户。对比强烈,正昭示出一个由被动赔款国,转而塑造契约信用国家的裂变。
1964年,中国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向莫斯科一次性了结所有剩余卢布贷款。本已注定紧张的中苏关系,在此刻出现了难得的交汇点:口头争执依旧激烈,账面却一清二楚。莫斯科《真理报》的评论用了“令人惊异的准时”来形容。对新中国而言,兑现承诺不是讨好他人,而是为后来者奠定可持续的外部信用通道——这在此后获取西德、法国技术设备的洽谈中展现出立竿见影的增信效应。

如果把十九世纪列强的炮舰比作冰冷锁链,那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中国无疑选择了剪断枷锁再扭头走人。清政府与民国留下的巨额对外债务,本质是强权下的不平等契约;解决它,需要法律武器,也需要政治魄力,更需要一套能在国际舞台上被听懂的叙事。毛泽东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注,外交部则用成堆法律文件和硬碰硬的谈判实践去完成了这道历史命题。
当年东交民巷的洋行招牌如今已难寻踪影,旅顺军港重新响起的是人民海军的汽笛,天津海关关徽里的“DRAGON”被磨掉,换成篆书“海关”。七亿多两白银这笔旧账,从文件夹里被划上红杠,成为博物馆里的展柜展品。历史学家在案卷末页留下简要备注:此案结,未付。
易倍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